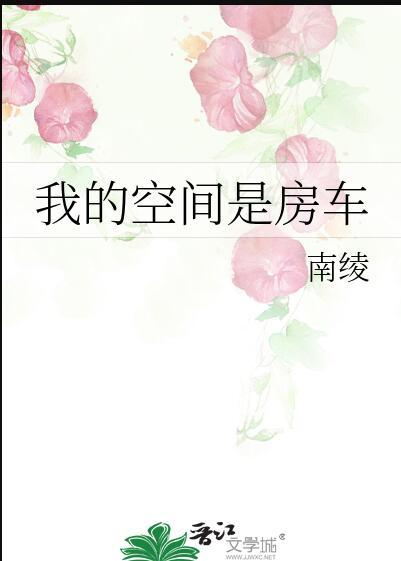乐天小说>臣尽欢 > 第4页(第1页)
第4页(第1页)
不知过了多久,就在阿九的神思抽离的前一刻,珠帘后方终于发出了一丝响动,似乎是青瓷相撞,清脆得悦耳,良久,一个声音传出来,仍旧波澜不惊,&ldo;你重伤未愈,起来吧。&rdo;阿九低声应是,这才从地上爬起来,目光不经意扫过珠帘后头,隐约瞥见一抹月色的白,干净得不染纤尘。她心下皱眉,隐约觉得眼熟,似乎……似乎在何处见过。然而未及细想她又移开了眼,敛眸在一旁站定。&ldo;你说……昨晚府中有刺客潜入?&rdo;珠帘后的人又徐徐开口,语速仍旧和缓,却透出寒意。脑子里回响起听兰的告诫,冷汗在刹那间浸湿了小衫。然而她面上却一丝不露,微微颔首,仍然没有丝毫的犹豫:&ldo;是。&rdo;&ldo;很好。&rdo;那人嗓音里沾上三分笑意,&ldo;宋同知,你听清楚了?&rdo;阿九面色微变,侧目扫一眼那群黑压压跪了一地的人头,听见宋直的声音响起,沉声道:&ldo;属下自知失职,恳请大人责罚。&rdo;&ldo;你险些误了我的大事。&rdo;里头的声音仍旧听不出喜怒,那人说完略顿,似乎思忖着什么,未几,又听闻他再度开口,语调里透出几分悲悯的意味,叹息道:&ldo;你的这些手下不中用,我的规矩你是知道的。至于宋同知你,死罪可免活罪难逃,姑且自剜双目,小惩大诫。&rdo;这话说出来,使得一室俱寂。宋直深深埋着头,双目赤红,沉默了良久方道,&ldo;……多谢大人,属下领命。&rdo;阿九静静地立在一旁,面无表情,垂在广袖下的两只手却死死握成拳,精心修剪的指甲很漂亮,此时深深陷入柔嫩的掌心,袭上一阵尖锐的刺痛。她能感觉到,一道阴冷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,带着探究的意味。分明是和煦的春令天,金色的日光透过窗格上的万字回水纹倾泻而入,不偏不倚照在阿九身上,她却如置冰天雪地。冷汗顺着耳际的发滑落下来,良久,珠帘后的男人又道,&ldo;行了,都出去吧。&rdo;阿九闻言微微缓了口气,紧绷了多时的身子骤然一松,将将转身提步要走,他再次开口,简简单单的三个字,钻进耳朵里,令她不寒而栗。&ldo;你留下。&rdo;☆、霜雾重&ldo;你留下。&rdo;在相府,乃至整个大凉,他说出的话便不容忤逆。阿九身形一滞,果然停住了步子不再走,一丝凉气儿从背脊窜上来,顷刻之间弥漫进她的四肢百骸,恐惧细细密密爬上心头。一众锦衣卫从她身旁走过去,途径时没有一个人侧目。不多时,屋子里便只剩下她同珠帘后头的那个人。房门从外头重重合上,隔绝开两种人的命运,阿九苍白的面容上印着一道淡淡的光影,窗扉洞开,她怔怔望着窗外。院中栽种着禾雀花,串挂成簇,深沉的紫,在金光照耀下却呈现出水红的意态,风拂花动,绚烂艳丽,昭示着无穷无尽的黯然生机。很多时候,人甚至不如一株春花,不如一粒草芥。阿九迟迟地回过神来,微抿苍白的唇,深吸一口气又吐出,规整规整思绪,这才缓缓转身。她微抬眸子,匆匆往那帘珠串后扫了一眼,却蓦地一惊,脚下的步子朝后退了两步--珠帘后的人已经不在了。她背上冷汗涔涔,面上掩不住的惊疑。一个大活人,还能凭空消失不成?她皱起眉,绞尽脑汁地回想之前的事。她一直在这个屋子里,并未见到他离去,更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自己甚至连一丝珠帘的响动,一丝脚步声都不曾听见。正惊忡,一个声音却毫无预兆地从她身后传来,阴寒冷冽,带着几分立在高山云雾间的肃清,&ldo;你在看什么?&rdo;五年的时光赋予阿九超过常人的自控力,然而此时,她还是硬生生唬了一跳,心中惊骇,一面往后退一面惴惴回头看背后的人,目之所及却令她呼吸都一错,脑子有刹那的空白,只凭空冒出了&ldo;惊艳&rdo;二字。三步的距离,不近也不远,足以令她看清眼前的人。阿九在相府长大,自幼习礼仪读圣贤书,也算得上有才有识。然而看着他,她却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一个词能用以描绘这样的美。也许是因为身上有苗疆血统,他承袭了一副极别致的五官,和汉人的循规蹈矩差别甚大。那副眉眼深邃异常,跳脱出任何人对美的想象,瞳仁如墨,画屏上的腊梅幽兰映入其中,那双眼便是天地间唯一的风景。他有颀长的身形,同她记忆中的蟒袍曳撒不同,他着常服,皎白如月,如墨的长发在耳后松挽,一缕发丝滑落,被那修长如玉的右手轻轻捻在两指间,侧目一瞥,眼波流转间尽是风华。乾字号的姑娘自幼习媚术,修得是如何勾引男人蛊惑人心。阿九此时却发怔,暗道媚术的最高境界恐怕就是他了,能以眼惑人。这时外头穹窿上飘来一簇云,遮挡了大半的金乌。日光的金色稍稍淡退几分,勾勒得廊檐柔婉青峰和缓,斜照向他,映衬他身旁的红梅霜雪,似仙,又似画中人。仿佛是注意到了她直直的眼神,他收回了落在画屏上的目光,微微侧眸朝阿九瞥了一眼,那韵致难以描绘,即使睥睨也显得从容而优雅,薄唇微启,轻声吐出了两个字:&ldo;斗胆。&rdo;阴鹜的眼,淡漠得教她浑身发冷。他周身的气息凛冽迫人,或许因为居高位,他言谈举止都能描摹出傲慢,俯仰天地,俯瞰芸芸众生,简短的两个字,霎时将徘徊在众生底层的阿九打回了原型。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只是转眼的事,她垂低了眸子,心头一沉,不假思索地伏膝朝他跪下去,&ldo;属下该死。&rdo;视线中只有那白袍一角,她匍匐得很低,心头堆满惊惶。居高临下,这是谢景臣最熟悉的角度。他俯视她,修长的指尖摩挲过腕上的蜜蜡珠,眼底无悲无喜,缓声问:&ldo;你真的觉得自己该死?&rdo;阿九身子一僵,半晌没有应声。曾数次耳闻他如何手段狠辣阴狠残忍,也曾数度耳闻他在大凉是如何兴诏狱,府中,乃至整个大凉的人都忌他如鬼神,方才亲身体会过,令阿九更加恐惧。相府培养了一大批的死忠之士,她是其中之一,本质上来说却是一件失败的作品,因为由始至终她都没能泯灭对死亡的惧怕。是以,尽管这时她口里说着自己该死,心里却根本不这样想她渴望生,渴望活下去,她真的很贪生怕死。半晌没等来个答复,谢景臣也不催促,只旋身踱到官帽椅前坐下来,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,唇角微扬,浮起一丝寡淡的笑意,&ldo;我不急,能容你慢慢想清楚。&rdo;这话说得不假。但凡同谢景臣打过交道的人,都知道他的性子。这是一个纠集了世间诸多矛盾的人,能达到这样地位的人必然有其非凡的手段。在大凉,谢景臣以行事狠绝著称,心狠手辣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这样一个人,应当暴虐成性,然而他却不是。他确实有一副世所罕见的好耐性。屋子里暗香浮动,玉漏滴答,阿九深埋着头,额贴着冰凉光滑的石板。这是个令人为难的问题,天底下恐怕没有人会真的觉得自己该死,她更不例外。听他的口吻,敛尽了一切情绪,根本无以揣摩。她沉默了许久,终于沉声道,&ldo;回大人,属下并不想死。&rdo;谢景臣面上仍旧没有表情,只兀自把玩手中的茶杯,极缓慢地转动,忽而一哂:&ldo;世上没有人想死。&rdo;略一顿,半眯了眼眸光扫向她,如斜视一具死物,&ldo;要活命,总得有活命的价值。&rdo;阿九没有吱声,只是僵着身子头俯得更低。又听见他的声音从头顶上方传下来,漠然疏离,&ldo;你杀了该与你一同入宫的女人,刺伤自己,又凭空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刺客,每一条都足以让你死千百次。&rdo;他语调平静,历数她条条罪状,听得阿九不寒而栗。她大为惶骇,昨日他不在府中,这些事是从何得知的?她细细回想,昨夜梅花亭附近的确并没有旁人,她能够肯定,便不会是有人通风报信……那是为什么呢?她冥思苦想,是哪里出了岔子,还是哪里露出了破绽?可是既然他已经说了这样的话,那是否就意味着……她这回难逃一死?是时谢景臣的声音又响起,他的目光落在她的头顶,冰凉如隆冬的风,徐徐道:&ldo;身上留了伤,入宫是不能够了。相府不留无用之人,你该明白规矩。&rdo;身子忽地一阵瘫软,阿九的十指在广袖地上收拢,狠狠粝过地面,传来钻心的痛意。拼死一搏么?方才这人无声无息到她身后,足见他的武功有多高深莫测,与他相斗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可是她不想坐以待毙,或许,能一试……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嗜爱+番外 废后芙兮 寻爱 桑榆未晚+番外 中校之舞+番外 是非+番外 相爱恨晚+番外 盲点 过期爱情+番外 痛爱+番外 将错就错+番外 你不知道的事 执念+番外 如果他知道+番外 愿赌服输+番外 我是如此喜欢你 顾盼生辉 林深终有路+番外 钟爱 我喜欢你很久了+番外